※本文摘錄《與山的一支獨舞:與自己同行,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》
📍瑞士‧霍恩利山屋
我該繼續走下去嗎?
現在並非進退兩難的局面……未來仍有機會捲土重來……不過,若真的放棄了,可能再也沒有這麼好的機會。我掙扎著,一顆心懸而未決……
 圖/三民書局提供
圖/三民書局提供
| 行程簡介 路線|霍恩利稜線(東北稜) 難度(IFAS)|AD (fairly difficult) 信心等級(commitment grade)|III 耗時|六小時上升、十二小時下降 天氣|晴朗 人員|一名 日期|七月十八日 技術裝備 四十公尺繩(8.5 mm)、健行冰斧、冰爪、快扣×2、有鎖×4、sling (60 cm×1、120 cm×1)、daisy loop×1、硬底鞋、吊帶、確保器(ATC)、普魯士繩環 其他 能量果膠×2、600 c.c.水壺、頭燈、手機、手套、羽絨衣、毛帽、Gore¬tex外套、雨褲、相機(Sonyα7R III+16-35 mm f 2.8 GM) |
七月十七日一大早,我離開營地,回到青旅寄放行李。
經歷了瓦斯罐被偷的事件後,我再也不敢把東西亂放,況且後面的旅程還有半個多月,可承受不起再弄丟東西。將要帶上山的裝備分出來以後,剩下的就鎖在置物櫃中。
離開之前,我偷偷跑到房間去看朗是否還在,想要跟他打聲招呼。但那當然只是妄想。兩天前我第一次登上冰河時,他就已經離開。進到了房間,那裡早已空無一人。
我刻意不和別人一起搭纜車。上了纜車以後,我橫躺在椅子上,短暫的十分鐘路程我打算放空自己。但不知為何,就算什麼都不去想,心情還是特別沉重。我打了一通電話給我媽。
「我在纜車上,要去爬馬特洪峰了。」
「今天嗎?我還以為你是明天去爬哩。」
「先到山屋去,然後明天一大早開始爬。」
「還是不打算找嚮導帶你去嗎?」我們早已討論過很多次,她依然很希望我能請人帶我。
「沒有,請嚮導太貴了。」我用很堅決的語氣說著,而且就算現在找也來不及了。
「要是四萬塊能換你一條命的話,就花下去吧,別省那一點錢。」
「太貴了。」我重複著,像是跳針的唱片。
「算了,講也講不聽。你自己小心,注意安全。」
「我知道,不用擔心。」其實我心裡也明白,就算說了不要擔心也沒用。做媽媽的,哪有說放心就不擔心的。
我們沉默了幾秒鐘,她開口說道:「如果真的不行就回頭吧,沒人會笑你的。」
「嗯……」我心裡再明白不過。
「有空就打電話回來,好嗎?」
「會啦。手機要省點電。」
「一路順利。」
出了黑湖(Schwarzsee)纜車站,離霍恩利山屋還有將近三小時的路程。沿著步道,一路遇到不少剛爬完要下山的登山者,清一色是兩人結伴而行,有些人會禮貌性地問我要去哪,聽到我說要自己去爬,大多數人都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。
就在快要抵達山屋之前,我發現好像少了什麼裝備,難怪從剛剛開始就渾身不對勁——
「該死!我的頭盔沒帶到!」
明明一路上有這麼多時間可以確認,我卻未曾看背包一眼。那個本應掛在背包上左右搖晃的頭盔,顯然被我留在山下了。愚蠢與自負讓我犯了一個要命的錯誤,足以令我立刻打道回府。 黑湖(圖/林雋提供)
黑湖(圖/林雋提供)
惡夢還沒結束。就當我開始確認還有什麼東西沒帶到時,手機的充電器不小心被我壓斷。
「我該繼續走下去嗎……」
到了山屋,我抱著最後一點希望,硬著頭皮問櫃檯有沒有出租頭盔,得到的答覆不出所料—
「對不起,我們沒有那種東西。」果斷拒絕了我莫名其妙的請求。
我尷尬道了句謝謝,趕緊轉頭離開,試圖掩飾自己不知所措的窘態。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在學校做錯事,被老師當眾斥責的那種羞恥感,簡直想把自己撕成碎片。我離開大廳走上樓,那木階梯給人不踏實的感覺,心情怎麼也輕盈不起來。
我到交誼廳的書櫃旁翻著馬特洪峰登頂一百五十週年的紀念書,那血紅色的山脊依然經典,不禁想起四年前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的激動。
在我懊惱不已的同時,陸續有人下山離去,天色也漸暗。山屋起初的人聲鼎沸轉為低聲細語。跟著這張照片來到這裡的我,在最接近夢想的地方被自己的散漫一棒打醒。更諷刺的是,幾天前我還在大談冒險的意義,如今卻連最重要的頭盔都忘了帶。
回歸現實,既然錯誤已經造成,下一步該怎麼做才是更應該思考的事。畢竟現在並非進退兩難的局面,此刻選擇回頭,未來仍有機會捲土重來。這次的經驗讓我意識到,自己的能力還不足以應付這座山,那是否該冒這個險?
即使最後說服自己出發,承擔被落石擊中的風險,但一想到我還有家人,並非真正的孤身一人,若意外真的發生,也是他們要飛過來善後。
人離開了,所有努力都付之一炬,並被媒體掛上斗大的標題「大學生玩命獨攀,葬身馬特洪峰」。人生就歸結在這短短一句話。
在這種緊要關頭,我被自己的愚蠢擾亂了思緒。我很清楚心存僥倖是危險的,但無法接受自己空手而回。確實,頭盔幾乎是無用的,但只要在攀爬的過程中,被一顆棒球大小的石頭砸中,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不過,若真的放棄了,可能再也沒有這麼好的機會。我掙扎著,一顆心懸而未決。
我帶著相機和腳架走到山屋後,想藉由攝影轉移我的不安。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。
山屋外的氣氛有些詭異。除了稜線上颼颼的強風之外,不時還能聽到雪崩聲迴響於山谷。由於馬特洪峰旁邊幾乎沒有任何旗鼓相當的高山,以致在這裡發生的雪崩聲,能透過山谷的回音展現更為浩然的氣勢。
我起初有些害怕,擔心雪崩就這樣鋪天蓋地而來。直到轟隆聲從咆哮轉為孱弱的低嚎,又變為寥然無聲時,我竟有種錯覺:「它是在怒吼嗎?或其實那只是它被誤解的哭聲?」
遠處因雪崩揚起的陣陣白塵,是山正在受苦的畫面;山谷裡迴響的聲音,是山正在遭受凌遲的哀嚎,它的體膚在山坳平坦處堆積成一片凌亂。山看似一動也不動地矗立著,近看才發現它原來是在顫抖,正在求救。
我重新審問自己到底在害怕什麼,是山,還是人類。
到了這裡我隨時能轉頭離去,但山卻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,屹立在這裡千萬年,面對不斷上升的氣溫,必須一層層剝除身上的血肉來爭取一線生機。
我感到害怕,害怕的對象是自己。
在彷彿沒有答案的深思之後,落日從山間雲霧中穿透出一道光,直直打在馬特洪峰上。夕陽的餘暉照亮山尖,雲霧消散,馬特洪峰的面容展露無遺。它好像感應到我的心情,溫柔說著:「烏雲總會散去。」
雪崩的聲音漸漸不再出現,冰河變得平靜,只剩下偶爾飛過的烏鴉,所有的不安一掃而空。所謂美景能夠治癒人心,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。我相信,它在乎著我。
美國的傳奇登山家吉姆‧布里威爾(Jim Bridwell)曾說:「你必須要保持信念,而不是抱有希望。」(You have to have faith, not hope.)

 烏雲總會散去(圖/林雋提供)
烏雲總會散去(圖/林雋提供)
因為希望是虛幻的。在自然面前,希望往往不堪一擊。所謂的人定勝天,在這裡並不適用。天,或說神、全知,才是能夠主宰生死的角色。
那就相信吧。即使很多事並非我能掌控,但這就是冒險的本質。
我回到房間,看向窗外,天空只剩下殘暉的微光與一抹奶油似的捲雲。山屋的靜謐讓人無比安心。
七點了,隔壁床的大叔早已睡到不省人事。也對,如果明天深夜三點就要起床的話,現在也該睡了。我這麼想著,在溫暖的被窩中沉沉睡去。
📍瑞士‧霍恩利山屋
「祝你好運,晚點見。」
有時候回頭並不代表怯弱。如果你在路上改變心意了,隨時歡迎你回來……
我早已習慣和自己獨處。從十二歲開始,我就在外面讀書生活,一個人搭車、一個人吃飯、一個人住。
一個人很寂寞嗎?說實話,偶爾會。但就像長時間身處在暗室之中,視覺會習慣低光的環境,即使是再弱小的微光,都能夠立刻發覺。若獨處能讓我懂得細察生活且更珍惜生命中的際遇,那也未必不好。
七月十八日凌晨三點,隔壁床的大叔搖醒了我。
「你要爬馬特洪峰吧?是時候吃早餐了。」他說完就轉身離去。
我下樓進到餐廳,攀登者都已經坐在餐桌上等待用餐。寒夜包圍整個山屋,用起霧的玻璃嚴正聲明它才是此時的主宰。
餐廳的交談聲降到了最低,不只是避免吵醒還在夢鄉的人,更像是害怕驚動某種沉睡在黑暗中的野獸,連腳步都輕飄飄的。
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早餐以後,由策馬特嚮導帶領的隊伍打頭陣出發。這是基於安全考量,為了避免攀登者走錯路,所有自組的攀登隊伍都必須排在嚮導後面出發。
我理所當然排在最後頭,看著一個個人影消散在黑暗之中。頭燈化為一朵朵在深夜裡綻放的白百合,搖曳在枯瘦的山脊之上。沒多久,山屋裡只剩下我和為我們準備早餐的女主人。
「輪到你了年輕人,要爬馬特洪峰的話時間不早了。」剛整理完餐桌的她說。
「該出發了。」時鐘標示四點整。是啊,還真是不早了呢。
「如果不確定是否要出發,你知道你是隨時能夠回頭的對吧?」女主人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不安。
「我知道……」這次我終於承認了,我的不安是真實存在的。
「有時候回頭並不代表怯弱。如果你在路上改變心意了,隨時歡迎你回來。」
我說不出任何話,只能姑且點頭作為回應。
「祝你好運,晚點見。」女主人臉上的表情比我還要有自信,彷彿她比任何人都相信我能夠辦到。
書籍資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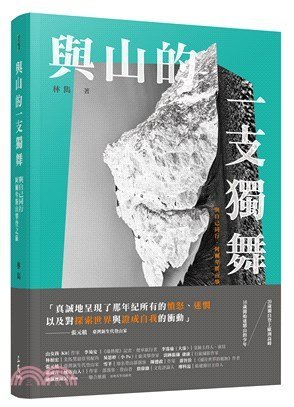
書名:與山的一支獨舞:與自己同行,阿爾卑斯山攀登之旅
作者:林雋
出版社:三民書局
出版日期:2021年10月15日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