※本文摘錄自「明天到阿爾卑斯山散步吧。」
多洛米蒂山脈的女王 馬爾莫拉達山

來到了登山的最後一天。要挑戰的是多洛米蒂山脈的女王—馬爾莫拉達山。據說馬爾莫拉達山有冰河流經。看見冰河也是我生平的首次體驗。
早上八點從旅館出發,坐車前往馬爾莫拉達山麓。原本有纜車可通往中途,卻已進入冬季停駛期。在山麓悠閒地做著木工的纜車工作人員,特地為我們啟動一臺纜車。
這臺纜車是座很奇妙的乘坐工具。有點像小型的籠子,站著搭乘。一次最多只能載三個成人,發出嘎嗒嘎嗒的聲音緩慢地往前行。
因為只有一臺,只能一次先送三個人抵達登山口,再返回載其他人,往返比想像中還要花時間。在等待纜車回程的時間,做木工的纜車工作人員和我們閒聊,滿臉笑容地問:「義大利怎麼樣?」、「人很親切嗎?」等等。
我回答:「東西很好吃,人又親切,簡直無可挑剔。」
「那嫁來義大利吧!」
他對著我眨眼,是位臉和鼻子紅紅的,體型圓胖的開朗歐吉桑。
我和鈴木,還有馬立歐的太太清香,三人一起搭纜車。纜車的速度慢到讓人瞠目結舌。在慢速的移動中,馬爾莫拉達山的全貌也徐緩地展現在眼前。

一片雪白!眼前矗立的山被雪覆蓋著,無人的滑雪場。
「為什麼稱這裡是多洛米蒂山脈的女王,就是因為被雪覆蓋的凜然樣貌,猶如穿著豪華禮服的女王一樣。」
清香如此說明。話說回來,昨天爬的山稱為「沙索迪史特里亞」,意思是「魔女之山」。多洛米蒂山脈有魔女,也有女王。
突然,站在一旁的鈴木唱起:「一片雪白的山,在朝陽的照耀下……」事實上,矗立的山確實在朝日的照耀下呈一片銀白色,但和這首歌的開朗氣氛相反,此刻讓人感到一股陰沉的恐懼。鈴木也不是以開朗興奮的心情唱歌,而是帶著嚴肅凜然的表情。
看起來緩斜的坡道,一旦真的開始健行就發現完全不是如此,結冰的雪變成滑溜的山路,看來一點都沒有融化的跡象。從之前的經驗看來,光想像就知道是一條險路。我不由得呢喃著,沒問題吧。
「小事小事,沒問題的!」
清香開朗地搭腔。年過五十的清香和馬立歐是現役的攀岩登山家。
最後一臺緩行的纜車,要把全部的工作人員和機材都運到登山口,看起來得花上一小時吧。在此地,或應該說東京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,時間之流是如此的緩慢。
馬立歐幫我連接繩索,穿上釘鞋,拿起雪杖,終於要開始行走了。雪果然凍結成冰,釘鞋像刺在雪上,我們一步步緩慢往前進。從遠方看起來坡度和緩的山坡,果然很陡峭,根本無法走直線,而必須左右迂迴才能前進。
當我往回望時,纜車乘坐處已經被遠遠拋在後方,變得渺小。但歐吉桑使用電鋸的聲音卻依然聽得見,可見山裡之靜謐。
「我三十年前來的時候,更下游處有冰河。」
馬立歐說。剛剛走過的登山口附近,以前是冰河。冰河漸漸融化,現在得到山頂附近才能看到。
在馬爾莫拉達山,不論是聳立在我的前方,或是在我後方像尖塔般突出雪層的山巒,都是如此動人的美景,但我卻只能顧及腳下。我只能看著偶爾露出的岩石肌理、在陽光下閃閃生輝的白雪,及穿著不習慣的釘鞋的自己的腳。
在景色單調到無法辨識的山路上默默地走著,腦袋也漸漸變成一片空白。雖然身在白雪之地,身體卻越來越暖和,甚至覺得熱了起來。沙沙沙,踏在雪地上的聲音不斷響起。
我踩到的雪變成小碎冰離開地表飛濺上來,然後往下落去。沒有任何遮擋物,只是往看不到盡頭的下方落去。看著往下滾落的雪,我不禁心生畏懼。不自覺地想像著,要是自己的腳一滑,整個人會像雪一樣滾落下去吧。我緊握著和馬立歐連結的繩索。有馬立歐在,就沒問題,我這麼對自己說。害怕的心情才稍微退去。
登山不只是單純地踏出左右腳即可。如果沒有對同伴的信任,根本無法成行。見到馬立歐不過是幾天前的事,但我卻視馬立歐如舊識的導師般信賴著。
我們在山斜面蛇行前進著,明明看得見山頂就在前方不遠處,卻始終無法靠近。天空和平常一樣在上方無限延展著。雖然沒有確切的感覺,但確實一步一步地向天空接近。
鳥在天空飛翔,和烏鴉有點像的黑色小鳥,從第一天就時常出現。或許有著人類會分享食物的記憶,總是飛到近處,用清晰的聲音叫著。平常總覺得鳥會飛是理所當然的事,在高山上看到鳥在飛翔時,卻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。流了滿身大汗,抑制著心裡的恐懼,好不容易才爬到這裡,和這樣的我相較,鳥是如此輕鬆自如地飛到相同的高處,而且還能飛得更高,反而是鳥才以不可思議的感覺看著我們吧。
映在鳥眼裡的是什麼樣的風景呢?馬爾莫拉達山、背後的山巒、遼闊無際的湛藍天空,還有費盡千辛萬苦,花了好長的時間才爬到這裡的我們,在鳥的眼中是如何看待的呢?
徐徐的微風輕拂著完全沒有人類足跡的白雪。雪像霧般往上飛舞並流動著。
對了!我還有得問馬立歐的事。我突然想起,對著繩索前方的馬立歐問。
「馬立歐,你之前說對天主教有一種違和感,對吧?佛教就沒有嗎?」
「沒有違和感。」
馬立歐配合我,腳步放慢地繼續往前並隨即回答。
「為什麼呢?佛教的什麼地方吸引你呢?」我又追問。
往前走的馬立歐小心翼翼地選擇用詞,沉靜地說明。
佛教和禪合而為一,只是靜靜地等著人自己頓悟。這只有自己才能知道。禪的境界裡有著什麼,只有自己前去,只有自己看見,才能了解。自己根本沒見過的事,只用語言來說明,就硬要人相信,我怎麼也無法去相信。因為那些不是靠自己的眼睛看見的,不是自己親身體驗的。而佛教就非如此。如果不自己去看、自己去體驗,就永遠不知道,不得不自己去尋找。他認為這樣的教義和自己的本質比較相合。
此時馬立歐停頓下來,回頭看著我。
「我們已經來到冰河之上。」他笑著說。

「咦?」
馬立歐蹲下來,用雙手挖著地上結凍的積雪。下方出現的確實不是看習慣的岩石,而是半透明的冰層。
「啊!」
我更加驚訝,也學馬立歐挖起雪來。不論往下挖哪一處的雪,出現的都是厚厚的冰層。
我驚訝得吐不出任何詞語。在雪的覆蓋下,根本看不出哪裡是冰河,但腳下的釘鞋踩下去時,確實和踩在岩石上的觸感不同。發出鏗鏘的堅硬聲音。
我想像中的冰河應該是像一條河的樣子。走在雪道上,不久路到了盡頭,然後像都市裡流經的河川一樣,是在較低處結冰延展開來的冰河床。我的想像也太幼稚匱乏了。馬爾莫拉達山的冰河其實是流經岩石和岩石的隙縫間。
菅原對我說明,如果沒有積雪的話,冰河可以看得很清楚才是。在茶色的岩山正中央,白色的冰河蜿蜒地向前流,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風景。我想像著蘋果派的中間,有一球白色香草冰淇淋融化流向四方的模樣—這也是個幼稚的聯想,但應該不會和現實相差太遠吧。
菅原進一步說明,馬爾莫拉達山的北邊,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處之地的北側,幾乎一整年陽光都照射不到,所以冰河才永遠無法溶化。這條冰河從何時開始就是冰河啊?實在無法理解的我,不由得發出這樣的疑問。何時開始?應該是很古早以前吧……菅原苦笑著。
馬立歐說,積雪堆成的冰川,還在四處形成了巨大凹洞,稱為冰隙。
走到凹洞旁往下望,黑暗中有一個開口。所站之處也幾乎快要崩落,冰隙又即將形成。我太害怕了,以致於無法再往凹洞靠近。
往後退了幾步,怔怔地望著不知延伸到何處的黑暗,「啊!」地叫了出來。我明白馬立歐說的話了。不是自己的眼睛親自看到的就無法相信,意味著馬立歐的宗教觀,也是登山的初衷,不是嗎?
再度往山頂前進的我又問了馬立歐。
「不論是相信神或是登山,對馬立歐來說是一樣的事吧。」
「的確是。」馬立歐立即回答。
「那裡有山,爬到山頂就能看到那邊的風景。在沒有爬上山頂的情況下,我不想推測看不到的風景。用自己的雙腳攀登,就能看到從山上遠眺的風景。不用自己的雙眼見證就無法相信。相反的,用自己的眼睛見證過的,只能相信了。因此,對我來說,山和神都是一樣的。」
馬立歐說到此處,停頓了一下,思考之後再追加說明。
「登山時腦袋變得空白,和禪一樣。坐禪時,也是要讓自己放空,然後體驗自己和天地一體的感覺。登山和坐禪其實很像。」
對於馬立歐的話,我心有同感,因為這也是我的想法。
不使用別人的詞彙,不輕易相信別人說的話,用自己的手去碰觸,用自己的眼睛去感覺。這是我在寫作時,對自己的唯一要求。
馬立歐說的話也完全一樣。「用自己的雙眼去見證」,肯定比我想像的更加困難。聽著馬立歐說的話,我暗忖。
最初聽到馬立歐這個人的背景時,其實我有點無法理解。現役的攀岩登山家,同時擔任登山導遊教師,自家也提供住宿,並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說佛。還無法將登山和禪聯想在一起的我,起初認為馬立歐一定是個怪人吧。但其實完全不是,我大錯特錯到羞愧的地步。眼前是一個用自己的腳爬上山頂,用自己的眼睛見證,只是想實踐這麼單純卻如此困難的事,以幾乎嚴苛的真摯追求著自己信念的人。
前方的冰塊突然從雪中飛了出來,像是突然打來的浪,瞬間在空中被凍結了起來。用手撥開突起的雪,突然出現半透明的冰。哇!是貨真價實的冰柱啊。我又像傻瓜一樣再度受到驚嚇。
馬立歐用尖鎚子把冰削了下來,並把鎚子交給我,要我也試看看。我用力地往冰柱打去,冰柱破碎,白色的小冰塊四處飛散。我們把冰塊放入嘴裡。雖然只是一般普通的冰塊,卻是經歷了數千年時間的冰柱。啊!我真想把它放入威士忌裡來喝啊。
前方的道路充滿了隱藏的冰隙,再走下去很危險,放棄登頂,就以這裡為此次的終點吧。馬立歐這麼說。我們照例握手代表此次的登頂結束,接著在冰突起的下方休息。
「這裡大約有多高啊?」
「大約超過三千公尺吧。」馬立歐回答。
三千公尺!聽說富士山有三七七六公尺。我現在所在的高度只比富士山頂再低一些,也是我人生中待過的最高點。

雲在視線之下,像細帶子一樣水平延展開來,群山的山頂突出雲層間。我在比雲還高的地方,而且是用自己的雙腳爬到這個位置。
我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路途,在全白的山斜面上有著彎彎曲曲的足跡,小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。而且,雪面的下方是看不到盡頭的冰河。那是在我出生以前,無法明確回溯的遠古時代就結成凍的水流。凝視著前方的風景,我感覺看到的不是雪山的斜面,而是巨大的時間。
所有的聲音全被雪吸收,冰凍的河川一動不動,全然被寂靜包圍的光景中,我的內心卻有著激烈的海浪翻滾著。這激烈的波濤不是因為河流,而是時間流逝的荒渺不經。冰河在人類出現,開始經營社會生活的更早以前,就存在於此,靜靜地看著出自人類之手的事物變遷。
啊!此刻的天空。這片天空、彼端的山巒、雲海、巨大的冰河、寂靜。即使親眼見證,也無法立即有什麼改變,但如果不來到此地,以自己的雙腳走到這裡,就一輩子也看不到眼前的風景。看不到就等於不存在我的面前。
走路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。今天一整天做了什麼?一整天都在走路。只是一直不斷地往前走,一步步緩慢的前行。光是這樣,現在的我竟然如此接近天空。在被完美的寂靜包圍之下,在宛如不存在地球上的風景前。這巨大的時間流逝感,此刻寂寥無比的光景,只要走路就能抵達。至今為止不存在的世界,如此真實的出現在我眼前。
而且,只靠徒步,透過這麼單純的一件事,我感覺到遇見馬立歐的真正意義。
「馬立歐,請問alpinist 是什麼意思?」下山時我問馬立歐。
「阿爾卑斯山的登山人。」
「這裡也是阿爾卑斯山?」
「嗯,是阿爾卑斯山啊。」
「那麼我也是alpinist 了。」我厚臉皮地說。
「對啊。角田小姐也是alpinist 了呢。」
馬立歐認真的點點頭,讓我覺得從心底暖了起來。
下山後,我們在山麓的咖啡館休息,喝義式咖啡、吃三明治。話說回來,今天我們什麼都還沒吃呢。只是專心一意的走路,完全忘了肚子餓這回事。
我們要在這裡和馬立歐及清香道別。每天一起吃飯,每天一起走路,真不敢相信就要別離。不顧我此刻的感傷心情,吃完輕食的馬立歐只爽颯地揮揮手。
「那麼,再見了!」
他輕鬆道別後,就鑽進自己的車子裡。
我們包圍著馬立歐的車子,向他道謝和道別。清香坐上前座後,馬立歐的車子駛出,一下子就消失在山間的道路上。
我從馬立歐身上學到的,除了登山之外,還有更多。輕鬆地道別也很像馬立歐的作風。短暫的分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我們已經相遇了,而且擁有一起走過的回憶。
回頭一望,多洛米蒂山脈的女王在雲層上方稍稍露出了頂峰。
相關文章
書籍資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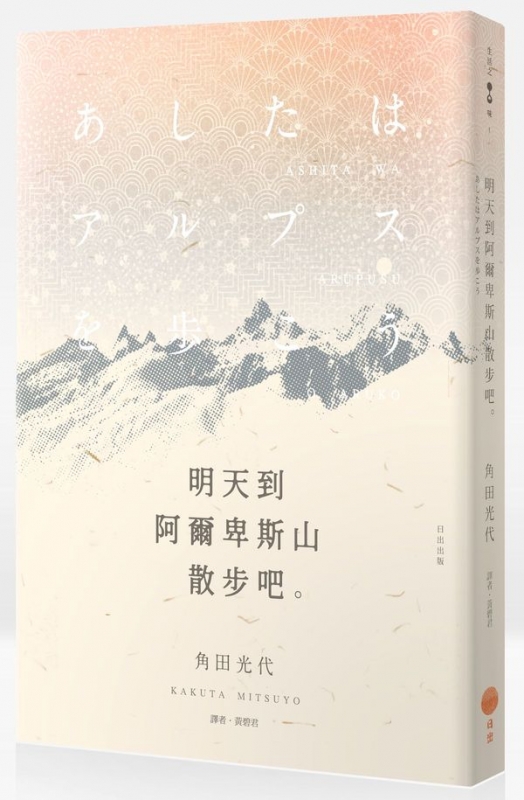 |
書名:明天到阿爾卑斯山散步吧 作者:角田光代 譯者:黃碧君 出版社:日出出版 出版日期:2014年10月02日 |
更多文章
- 多洛米提山脈
- 少女峰區健行(1):從Rosenlaui到Grindelwald
- 五湖健行—Grindjisee-Grünsee-Moosjisee
- 攀上瑞典最高峰 Kebnekaise
- 奧地利終於下大雪之山林假期(上)